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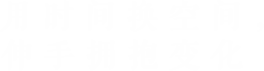
“你必须拥抱他。”
与澎湃新闻记者见面那天瓢泼大雨,即便从港岛回新界打车花了一个多小时,赵磊还是喜欢这座城市带给自己的熟悉和舒适:“起码下雨天走在人行道上,踩到的砖头不会迸水。”
赵磊去年有了第一个孩子,他想得最多的不是“上车”(购置第一套房子),而是如何从一年前做电商的失败中积累教训,重新开始跨境医疗的创业。从香港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一边从事金融工作一边做“港漂圈”,今年是他在香港的第九年,他已拥有16万微信粉丝。
34岁的张翠是4个孩子的母亲。当2015年刚得知有了第四个孩子,她有些抓狂地指着丈夫嚷,“我左右手各牵一个,怀里兜一个,多一个安哪儿?”
她们一家住在港岛东尾巴上一套四十多平方的房子里,2007年从广东肇庆嫁入香港以来,这是她住过最宽敞的地方了。夫妇俩当时以160万的价格购入,现在房子已经飞涨至350万,但即将到来的新生命会分去他们本来就不多的空间。
丈夫让她自己做决定,无论如何,他会尊重她。最终他们生下了这个孩子。
回归后,像赵磊、张翠一样的普通赴港者正为他们的“香港梦”而奋斗:底层的为了物理的生存空间营营役役,中产们则循着机会找寻向上的空间。在这场同时间的拉锯战中,新港人们即便偶尔错觉浮在空中,也仍对在这弹丸之地辟得一席立足之地满怀希望。
两地
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开数据显示,在拥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过去二十年里,超过90万内地人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民。他们在正式拿到香港身份证之前,一脚踏在香港,一脚踏在内地。
张翠和先生曾是中学同学,先生念高中时随父母去香港,拿了香港的身份证。分别十年后,二人在肇庆重逢,聊起少年往事,情投意合,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2007年两人结婚,让张翠心焦的不是两地六小时的车程,而是每月回内地一续的港澳通行证,续一次证就需要等待两周。“一个月奔波一次,大着肚子也要乘车回去。那时我没有身份证,父母也无法以‘探亲’为由过来香港照看孩子。他们至多只能来一周,两天还浪费在路上。”
2017年6月初,香港,家庭主妇张翠在家中照顾四个孩子。自2007年从广东肇庆嫁入香港以来,她与丈夫、孩子住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图
“到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政策有所改变,夫妻关系可以在港停留三个月,”张翠说,“但那时候还是比较严格,需要有医生出具证明信,说明孩子在香港出生,才可以通关。”
她没有完整地坐完月子,就急匆匆赶回老家续证。公公要上班,而婆婆身体不好,她几乎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她还没有带孩子经验,给孩子冲凉都要等先生回来。
带着两个孩子,回趟家太不方便了。“以前还可以坐船,从尖沙咀坐船回我家。可能乘船的人少,现在取消了。我喜欢坐船回家,因为带着小孩,船的空间比较大,方便孩子走动。”船行取消后,她只能带着孩子挤进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车车厢回家。
那段时间里她没身份,无法在香港找工作,她曾考虑过回老家工作,“没工作的感受会和生活脱节,即便有朋友联系,但因为不在一起生活,还是有很多不同。”但她的丈夫接受不了刚结婚不久就分居两地,而且她回广东月收入一千多,差不多等于从香港来回广州的车旅费,一来一回等于做了无用功。
直到她在四年后拿到单程证,一切才稍稍安定下来。
单程证是1980年10月后的产物,所有内地居民赴港定居必须向内地公安部门申请单程证,只有在香港有亲人的内地居民才可申请赴港定居。因单程证名额有限,申请的人需要轮候,回归前有个案轮候长达10多年。
“新移民申请来港团聚,由内地公安局审批及分配名额,一般排队需要四至五年。”张翠解释说。
重新工作的想法一再被搁置,四个孩子让她无暇去考虑其他,“我现在没有工作,因为孩子放学时间有时挺早,小孩子才两岁半。这边的幼儿园两岁便可入托,规定是三岁入学。我之前找了一些超市收银的工作,但是时间不合适,就算了。”
今年是张翠来港第十年,等身份证满七年,她可以换香港永久居留证。
蜗居
新移民们最初的生活安放在几平方米的火柴盒空间里。
罗霞1997年拿到香港身份,跟丈夫和三个女儿住进的是3平方米的劏(tāng)房。这间“劏房”的房东是把一间三十多平的屋子隔成了七间,洗手间和厨房公用。
在这样局促的空间里,碌架床(双层床)是标配。三个孩子睡上层,夫妇俩睡下层。让罗霞心痛的是,有次小女儿刚睡醒还犯着迷糊,从上层一不小心摔下来,把手腕摔断了。
每天做饭也要算准时间,仅能容纳两个人的厨房不允许罗霞在里面磨磨蹭蹭。她很快发现七户人家中只有四家会自己做饭,她会精确地计算好时间,在其他租客还没回家前把菜都做好。
房间里如果放一张桌子门就开不了,于是她会在上层的床护栏上架一块板,板的另一头恰好搁在对墙的支架上,把热菜端进房“就摆在天上晾”。
好在,她们一家五口现已住进公屋,三平方变成了三十平方。对空间的诉求经过极度压缩后,空间哪怕只扩张一点,身处其中的人都容易感到满足。罗霞说到一家人所住的深水埗公屋,眼里满是喜悦,她没想到有一天“居者有其屋”会在她身上兑现。
公开资料显示,新移民底层家庭并非只集中在天水围,还有屯门、油尖旺、黄大仙、观塘、彩虹、长沙湾、深水埗、石硖尾等地。
张翠40平方米的家已算蜗居族里宽敞的,但四个孩子和丈夫的东西如何收纳成为伤脑筋的问题。她的家里挂着好多绳子,绳子上一层层挂着衣服。尽管能看出她在记者拜访前收拾过家里的东西,但还是没有腾出更多的空间让孩子可以随意跑动。
家中空间逼仄,张翠常会选择把孩子带到楼下不远的公园玩耍,等孩子再大些可以让他们去图书馆。
香港中环街景。 /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住惯老家宽敞的大房子,张翠的母亲第一次来他们的新房,不悦地问了句,“怎么在房里走到哪都会撞桌子?”她母亲第一次去香港的菜场就被菜价吓到了,她让对方称五块钱的菜心,本以为对方会装好一大把递给她,没想到对方没伸手拿钱,倒是问起,“你是要几根菜心?”她这才发现,内地每斤单价一块的菜在这里都是十几二十块。
张翠早已习惯生菜六七块,菜心十多块。有次丈夫问她为什么连续好几天都买同一种菜,她只能不好意思地说,挑最便宜的买,一下子煮许多,分几天吃。如果赶在收摊之前买,菜会更便宜。
令人欣慰的是,成长在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乖巧懂事。
“我的四个孩子中,老大和老二选择同一个兴趣班,我可以省心一点。大女儿现在才三年级,但已经很会照顾小妹妹了。养小孩有很多开支无法算,不像水电费那么具体。也会教育孩子合理消费,多数时候会用奖励的形式送孩子礼物。”张翠说。
尽管极尽节俭,张翠还是大手一挥给大女儿买了台钢琴。烤漆黑的钢琴放在本就不大的屋子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希望孩子不要因为空间狭小而错失追逐梦想的机会。
触梦
香港芭蕾舞团前首席演员吴菲菲熟悉踮起脚尖的感觉,一如她从东北来南方城市香港后的生活状态。
2003年,17岁的吴菲菲还是沈阳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学生,她去香港芭蕾舞团交流,直接被选中发了聘书。她还能记起那时在港铁上激动地用IC卡给父亲打长途,父亲鼓励她,“就留在香港试试吧。”
吴菲菲在沈阳是舞蹈队里的佼佼者,可来了香港优势却没有了。香港的舞蹈排练和内地重复练习基本功不同,更看重个人的悟性,这让过去依赖老师的吴菲菲有些迷惘。“老师讲求高效,脑子都转得飞快,他只是一个给你提供知识和服务的人,不会手把手教你。”
2017年6月2日,香港,香港芭蕾舞团前首席演员吴菲菲(右)正在练功房排练。 /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图
她从第二组群演的替补做起,可跳了一两年还是原地踏步,每个月只有五场演出,芭蕾舞团的两组群舞已经是足够的了。如果幸运的话,她可能是第二组的群舞,如果不幸,可能连第二组的群舞都排不上。“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无形当中会有些打击和阻碍。觉得自己走得不是很顺,那时有点灰心,想要放弃。”
有天她结束排练准备回家了,回头检查有没东西落下时,却发现同一批进入舞蹈团的一个日本女孩和一个英国女孩还在练习。“虽然合约说到六点钟大家可以下班了,可是人家还在练,我就有点不安。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是自己不努力。”
开始积极投入排练后,“表情和气场都是不同的。”工作日是每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半天,她结束排练就去看其他人练习,领舞、独舞。
每晚结束排练她太累,就会躺在地上半个小时再爬起来。揉揉腿,拉拉筋,放松下肌肉。“七八点到家,买外卖放在家里,一点都吃不下去。逼自己吃,觉得不吃的话没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 有时吃两口休息下,然后就睡着了,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她慢慢有了机会,跳《蓝鸟》的双人舞,2012年凭独舞《一间她自己的房间》获得香港舞蹈年奖。
2013年,吴菲菲左边的胯部严重受伤,无法走路,睡觉平躺在床上都痛。她做复健、理疗,恢复又复发,反反复复,一直吃止痛药。那时还一直在演出,跟国外请来的一位嘉宾演员跳双人舞,她不想放弃,但也无可奈何。
2014年7月她正式离开了舞台。“虽然我在舞台上跳舞,谢幕的时候有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当时觉得什么汗水、泪水都值了。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对教课也很感兴趣,不一定要自己跳,学生学会了拿成绩了,我反而会更有成就感。”
在她看来,香港本地艺术发展比较晚,主打是金融。她在香港芭蕾舞团这些年,舞蹈团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她觉得所有的辛苦没有白费。
她开始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时间就是那个答案。时间长了,就会对这个地方有熟悉的感觉,哪怕空气的味道,建筑的风格,沿途行人的穿着。每次一下飞机,我就知道回到香港了。”
创业
1997年6月,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赵磊从哈尔滨去北京参加夏令营,名为“我去香港上大学”。“那么巧,我自己都服了,可能当时就埋下了来香港的种子吧。”
2008年,赵磊到香港念机械工程的研究生,这个来自东北的男生一开始有些不适应,“那时我想吃一些好吃的,都会去深圳,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如此熟悉,道路的宽度如此熟悉,电梯的速度如此熟悉,人们的说话方式也是我熟悉的。”
2010年,他投身金融行业,在一家金融机构做二级市场投资,同时经营着“港漂圈”的微博。
“每年在香港的港漂大概有3.3~3.4万人。”赵磊将港漂这一人群分为这几类,第一类是从内地到香港读书的学生,第二类是直接从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专才和优才。还有一类是内地人去了海外念书再回来香港。
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公立大学正式面向内地招收自费本科生,招生范围仅限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6个省市。香港在同一年施行的政策还有向内地开放自由行以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赵磊把这些政策放开视为港漂形成的背景。
在他看来,“港漂拥有几个属性,第一年龄在20到40岁,第二受过高等教育,第三他到了新环境,没有旧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创新去积累资源。”
2013年,赵磊辞去工作,专职创业做“港漂圈”,他看好这个群体的发展。2015年他做跨境电商,2016年中段失败了。2016年启动运作跨境医疗,目标客户是更具视野的中产人士。
“资本普遍指望获得短期回报,青年人倾向于争取高工资而承担低风险,所以创业者要左手温暖右手,把痛苦当做快乐去欣赏,去体味……”他曾在2013年11月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像是预言了当下的自己。
从创业开始,他也更深刻地意识到香港这座城市对他的改变,“一定要往上走,它把你的时间感觉都调快了。”
这是专业和效率至上的城市调性所致。“比方说我们想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一般来说七天就成立起来了。有时候你(还可以)加急的,我之前成立一家公司,已经是一个月月尾了,到下个月月初就会有新的政策,可能收费就会更多,我就会紧急地问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结果对方给我加急,第二天就做出来了,超级快。”
这让赵磊偶尔变得患得患失。“创业会让你的心情发生很大起伏。一天醒来,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离你而去,又一天醒来,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向你迎面而来。”
他说自己目前不会考虑买房,坚持想把篮子里的钱用来创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为“上位”(升职)、“上车”(购置第一套房产)而焦虑,他更想拥抱新的变化。
新移民们至少都是愿意拥抱变化的人。赵磊说起,就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批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他们那一代,存在些被迫的东西,但只要肯努力肯拼搏,就会有相应的收益。那是一个你来到香港,只要肯做事情就可以成功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