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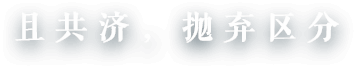
中国内地与香港只隔着一条深圳河,自西向东行走,河道渐窄,最后在沙头角陆地相连。
在沙头角中英街的两头,一边属深圳,一边属香港。
1973年,陈克治与女友李洁馨从深圳游往对岸的香港时,满怀对生活的憧憬,“周围很多朋友有亲戚住在香港,他们说香港的人有‘南风窗’,意思是房子向南,舒适。”
真正到香港后,迎接他们的是三餐无着,租住铁皮房;加班加点,夜深躺下,来不及回想过去就沉沉睡去。他们却鲜有抱怨,陈克治回忆,“我姨在香港独自撑起家庭的经济,日子虽清贫,几个孩子时时感恩,保持快乐。”
香港的人口数量长时期受人口迁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的人口增长主要是逃难后回归的居民,亦有一些是希望生活有所改善的移民。仅在战后一年内就有100万人从内地来港,在60年代,内地移民到港人数减少,70年代末又有大幅攀升。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邵一鸣在《内地移民对香港人口和社会的影响》一文中谈及,从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转向发展工业,内地来的移民正好带给香港需要的资金、知识和劳动力。
细数香港上世纪经济腾飞的细节,离不开“遮头瓦”下生存的内地新移民。他们每天做着辛勤的工作,从未断绝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唱《狮子山下》的罗文便是这群人中的一个,香港精神也正如他在歌中所唱:“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的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抵达
陈克治今年刚好70岁。6月1日下午,他爬到香港太平山顶,身手麻利地攀上一块高石,随即坐下,眺望港岛密布的高耸楼宇。
这些年,他和妻子李洁馨常会带朋友爬太平山,一起看看他们奋斗打拼过的香港。
从1977年开始,他每天清晨还会去香港红磡大环山游泳池以南的海湾游泳,风雨无阻。他背朝大海跃起,抛物线的路径扎入海里,海里是忆苦思甜的过去,抬起头来是钢筋水泥的现在。
陈克治的大女儿还在上中学时,曾带着一群同学回家。孩子们围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诉说如何从广州到香港,孩子们张着嘴听完,有些半信半疑。
轮到他的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时,他们不再对父亲的故事感兴趣,也从不过问。或是出于后辈了解历史的需要,或是不甘淹没祖辈体面的家族史,陈克治开始写回忆录。
陈克治回忆在港的半生经历。 / 视频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唐筱岚
60年代初到香港的钱洛深则在2002年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回忆录,两年后他溘然长逝。孙子钱笃诚如今年逾不惑,5月27日与记者见面时,他掏出祖父的这本回忆录,装订好的纸面已有些泛黄和卷曲,但不妨碍它完整地展开家族到港的过去。
二十多年前,钱笃诚和妹妹过年会随父母回深圳罗湖(原宝安县),那时他不清楚为什么父母要用“回”这个字。他妹妹稍大一些了会问,“为什么过年要去那边?我们家不是在香港吗?”父母不答,妹妹童年的好奇也就止于此处。
“有很多人不会想这些问题,要是我爷爷不这么写我也不会感兴趣。”钱笃诚试图到内地网站“知乎”上找寻答案。
1973年,当陈克治爬上吉澳岛岸边的时候,看到一些废弃的胶带和罐头,上面写有英文。他知道自己到了,因为当时在内地,“这些好东西是没人舍得扔的。”
当地农人惊讶于年轻人竟越过九号风球“黛蒂”安全着陆。
他随身携带的自制指南针、闹钟、干粮、干净的衣服都已经被夜晚几米高的海浪冲走了。好在,绳子没有断,一端环住他一侧脖子和另一侧腋下,另一端拉扯着李洁馨套着的救身圈。
他们在当地水警的帮助下顺利投靠了在香港沙田和田村当接生医生的阿姨。陈克治怕母亲挂念,到达后就给家里发了一通电报,“我们旅行结婚了。”当晚,陈克治在姨妈家吃了六碗饭,李洁馨吃了四碗饭。陈克治说,“阿姨家的表哥表姐习惯是不把饭装很满,那样不礼貌,像施舍乞丐的感觉。但我心里想,你装满一点(多好)。”
初到香港的钱洛深一家,到警署登记好身份证后拥有了合法居留权,也同时成为华裔无国籍人士。“爸爸到1997年回归的时候才得到特区护照,之前都是用身份证明书出国的。”钱笃诚说,祖父后来在香港开了饼店,而父亲则在日后成为了港府的公务员。
欧阳东是1979年从深圳蛇口到港的,曾在蛇口养蚝的他提前在内地蓄了两鬓的头发,看着“像香港人”,他换上当时香港流行的喇叭裤和花衬衫,怕在抵达市区之前被警察发现。“蛇头”收了钱,把他带上一辆小巴。中间有警察上来查身份证。他内心慌乱却故作镇定,还好他坐在最后,警察没有查到他就下了车。
他顺利抵达市区,霓虹灯闪烁中,他抱着新奇尝了口从未喝过的咖啡,深刻记住了这苦涩的滋味,以后再也没喝过。
揾工
迅速立足是新移民到港后最初的愿望,找工作在粤语中被称为“揾工”。
凭着阿姨在当地的威望,陈克治夫妇很快有了工作。几乎同时,广州的两家亲戚大摆酒席庆贺二人结合,而陈克治和李洁馨则在生产手表带扣件的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小时,领着五块钱的日薪,中午就着白开水咽下八毛钱一只的嘉顿面包,舍不得买其他同事喝的维他奶。
很快,二人又辗转到10块一天的纱厂做学徒。一个月学满后,就一人开一部织机,白班一天可以赚14块,上夜班会比白班多6块的加班费。“那时候香港的女孩不想做夜班,如果你不做白班做夜班,一天就有20多块。”李洁馨回忆。
纺纱的过程是这样的:棉花原料进清花机打松,再到梳棉机里把棉花梳成花卷,然后通过并条机牵伸加捻把它做成粗棉条,接着把粗的棉条打成比较小的粗纱,之后加工成像针织细线一样的细纱。有时候就连续站上16个小时,看到纱筒装满后停机换空的纱筒,没有坐的时间,喝水上厕所都很困难。有时候要围绕机器巡回跑,看打纱机有无断线,如果中途断了,要停下来重新接过,不然卷着卷着就飞起来,像下雪一般。
2017年5月25日,香港,陈克治和夫人李洁馨在海湾游泳。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图右:1973年夏天,广州宝岗游泳池,陈克治和当时还是女友的李洁馨在游泳池边合影。 陈克治 供图
下班后,二人的头上、身上常常全是白的棉絮。
夫妇二人是厂里的顶班王。那时厂里会发勤工奖给半个月不请假的员工,有些人想拿勤工奖,就找陈氏夫妇顶班,把当天工资给他们作为报酬。
初来香港,他俩晚上会做些错乱的梦,分不清自己身处香港还是内地。工作慢慢让人疲惫,二人基本沾床就睡。
纱厂是上海人开的,里面有些上海的老员工,在解放前就做这行,几十年如一日,现在反应慢了,工钱也少。多劳多得,工钱多少全看纱厂机头上的转速记录,陈克治工作了两个月后薪水就超过了他们。他觉得继续在纱厂工作似乎一眼能望到头,便想到了转行。
1974年,他进入了其士集团做电梯安装工人。
彼时,陈克治很喜欢听歌手许冠杰唱打工仔心境的《半斤八两》,“出咗半斤力/想话洛番足八两/家阵恶揾食/边有半斤八两甘理想/吹涨(出了半斤力,心想能拿回八两的工钱。现在工作艰难,哪里还有半斤八两这种好事,你奈何不了)。”
“只是安慰我们这些打工仔,你不要以为出了那么多力就有那么多报酬,没有那么理想的。我感觉这种写实的歌词反而让人坚强起来,还有一个鼓舞激励的作用。”陈克治说。
鼓励公平、多劳多得也令新到港的内地青年刘梦熊振奋。
20岁出头的广州青年刘梦熊初到香港时,在一家不锈钢餐具厂做工。他租不起房子,就提议帮老板看厂,让老板解决食宿。他买了一张折叠床,工人加班到晚上10点走了,他就在锅炉房洗个澡,把折叠床张开来睡。
第二天别人上班了,他就把床叠起来,放在门旁的角落。就这样,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七点半做到晚上十点半,每个礼拜天白天加班,只有礼拜天晚上可以喘喘气洗洗衣服。
不过,让他欣喜的是,当时他在内地农村一年赚127块,在香港一个月就拿到了300块工资。
70年代,刘梦熊还在工厂打工,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如果阁下对目前工作处境感到不满,而又胸怀更大的事业抱负,对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充满信心的话,本公司愿与阁下诚恳一谈”。
他满身油污,蓬头垢面地去面试,幸运地被这家日本的期货公司选中。
据界面新闻记述,“刘梦熊买来中华厂商联合会、工业总会等的会员名录,记下会员的电话、传真和地址。每天亲笔写下20封信寄出去,默默地创造着1%的机会——希望100个人里能有1个成为他的客户。”
奋斗
香港进入六月后,歇斯底里地湿闷起来,陈克治双腿的膝盖和左手手肘有些隐隐作痛。
那是老工伤了。当时他被安装电梯中失控的高速滑轮击伤导致手肘骨裂,医生动手术时帮他把神经移位,从此之后,他的左手肘部再也无法绷直。
他的手腕静脉处也有几道状如枝蔓岔开的疤痕,那是有次在工地踏空,一脚踩进洞里,手一撑地,工地上的锋利杂物把手划伤。
有时即便导轨很重,也要屏住气奋力安装。在井道工作,听到响声就要跳回楼面,有时跳得太急,撞到门框的钩子、钉子、木板,就会血流不止。
那时有一档《欢乐今宵》,是从晚上八点半播到九点半,周末会延迟到十点。他工作的地方隔壁就是民居,电视机的声音很大。
陈克治记得清楚,欢乐今宵的开场曲是“从白天做到现在,要休息一下吃个晚饭,轻松一下”,而结尾曲是“欢乐今宵再会,各位观众晚安”,但直到晚安歌唱完,他还没办法收工。
深夜回到家,他的孩子们都已经睡觉,而因为开工早,他上班时孩子们还没起床。“当孩子们在周末见到我,跟我说,爸爸见到你好高兴,其实我每天晚上都能见到他们。”
在经济腾飞时期,城市就像高速运转的滑轮滚滚向前。
最初,陈氏夫妇住沙田,要搭火车去上班。火车站很旧,轰轰隆隆的声音涌过来,车子没停稳二人就跳上车,“先上车后补票”——如果翻到月台对面100米的地方去买票就来不及上这趟车。
等到从尖沙咀火车站的钟楼出来,虽有三毛钱到红磡的车,他们还是选择步行。有次二人赶去上班走得太急,警察追上来问他俩,“是不是有人要抓你?可以找我们帮忙。”
白辉回忆,到港的最初两年自己尚处在兴奋期里,“什么时候知道兴奋期过了?开始感到累了。”
欧阳东起初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连续一两年这样的生活,逐渐感到力不从心:白天在制衣厂,晚上为了赚外快在电镀厂加班,实在熬不住只得请个下午假休息。在厂里,裁床是一条板子架在上面,他就在裁床下面的隔层睡觉,裁床上面人家在裁布,也照睡不误——不睡顶不住。
应对高速而拮据的生活,新移民们把“多快好省”的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
陈克治去弥顿道出名的烧腊店皇上皇,只买一块钱的腊鸭皮,分几顿吃。七点落班二人才去买菜,因快收档买蔬菜最便宜。去菜市场买不起鱼,只买两毛钱的鱼肠。床单都是旧的,舍不得买衣服,二人就穿表哥表姐扔下不穿的老校服。
在他们眼里,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充实,也有自由奋斗的空间。这种奔头几乎可以帮他们抚平一切伤痛。
共济
1974年初,陈克治夫妇从简陋的铁皮屋搬到附近沙田隔田村的乡村独立屋,租住花园内的一室一厅。业主是已过世的姓李老先生的两位遗孀——大李太和细李太(小李太)。
她们都是香港人,因为乡郊清净才在沙田买地建屋。细李太五十多岁,还很精干,儿女都搬去了九龙市区住。两位李太知道陈克治夫妇的身世,对二人格外好,租金也收得便宜。每逢假日或农历传统节日,她们的儿孙回来团聚,吃饭时必邀请他俩,将他们视如己出。
1975年,李洁馨怀上第一胎,那时她还在纱厂上夜班,陈克治已经转职为电梯安装工人,工作忙碌。有一天李洁馨下班回家,与往常一样和李太一起去墟镇的街市买菜,李太顺便带李洁馨去相熟的中药店(有中医师驻诊)开安胎药,到了药店,李洁馨突然因妊娠反应昏倒。
老中医了解情況后知道陈克治就在附近的工地开工,他让李太留在药店照顾,自己去工地找陈克治,好不容易才找到陈的工友。“他领我回药店,向我详细解释了我太太的情況。我耽误了他的诊症時间,但他没有特別收费,只收了安胎药的钱。”这些来自本地邻里的善意让“外地人”陈克治感觉格外温暖。
1987年,香港,陈克治一家五口在海洋公园合影留念。 陈克治 供图
为了节省上班时间,陈氏夫妇决定搬离出租屋,离别时与李太们依依不舍。后来,细李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去世,儿子生前的公司每月都会寄给她抚恤金,还承诺会协助她移民。
大女儿出生后夫妇俩还去探望过她,但十年前再去时,那间屋还在,按门铃却没人应了。
陈克治进电梯安装公司时才26岁,其他工友、包括师傅大都比他年轻,他们很跟潮流,知道陈克治是大圈仔(广州偷渡客),都常邀请他和太太参加他们的团建活动,诸如烧烤、游船、溜冰及代表公司去参加足球比赛……
几十年后工友聚会,常对陈克治的一段往事津津乐道:那时的年轻人都是李小龙迷,有次午休时间,几位工友争相表演李小龙的连环踢腿绝招和震慑敌人的眼神和吼叫声,“我那时和大家还不很熟,突然站起來,表演了一串自由体操的侧手翻接空翻动作,众人一下子呆了,都坐定不再表演。”陈克治说着笑了起来。
陈克治在电梯安装公司打了十年工才出来自己承包工程。十年间他搬了四次家,几乎都是搬去没有电梯的旧楼,有次还是搬上九层高的天台木屋。每次都有五六位或以上的工友义务当苦力帮助夫妇俩,省下了一大笔搬家费。“那些帮忙的大都是香港仔。”陈克治说。
在艰难揾工的生活里,内地来港的朋友间也相互扶持。
陈克治曾提到一位来自广州的高中校友霍之邦,虽然两人分属不同行业,也常互相帮助:因熟悉电梯结构,陈克治可以绕过公司帮单栋大厦的业主翻新电梯,报价只是公司的一半,所以很容易接工程。而霍之邦从事装修,粘胶板很熟手,陈克治就常请他帮忙,两人合作通宵一晚,各有两百多元进账——那时普通工人的日薪才三四十元;陈克治放假时也常在霍之邦的工程队里做装修兼职。
白辉也提到那时他在酒楼做侍应生,一旦一家酒楼倒闭了,几位同事就会帮忙一起找其他酒楼的门路,很快抱团。其中一位同事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归属
1995年,陈克治和妻子用435万在红磡购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目前房产市值已超千万,儿子和女儿们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这在空间普遍逼仄,地价寸土寸金的香港显得难能可贵。
白辉到港后在酒楼工作了12年,如今他手上的物业和店铺早已价值过亿。他向记者反复说,当时中环那些写字楼不是我们这种学历的人能去的。时隔多年,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从港大和港科大毕业后投身中环的金融业。
白辉的第一套房子在顶楼,空间太小,夏天又太热,他本想置换一套大的房子自住,于是买下了38万的楼花(注:意为还未建成的期房)。未料,三个月就涨了五万,几乎是他一年的收入,他就大胆出售了。这一买卖启发了他,他转手房产几次后自己开了房产中介公司,成天跑去各家地产公司找笋盘。80年代到1997年香港楼价经历过几次回调,但总的趋势是往上涨的,白辉转手来去中收益不俗。
2017年6月3日,香港,白辉站在太平山上看着香港的景色。 澎湃新闻记者 吴 越 图
挫折也碰到过。1997年到2003年,楼价跌去70%。即便如此,他还是看准银行利率走低至两个百分点左右对楼价的稳定作用,“比如我第二间房子是1990年花200万买回来的,升到1997年1000万,跌到2003年只剩下300万,我2005年把它以570万的价格卖出,买了这里1476尺(相当于140平方左右)总价1280万的海景房,现在升到3800万。”
1997年香港回归后,新移民(new immigrant)的说法被改为“新来港定居人士”(new arrival)。
白辉放弃了加拿大移民的机会留在国内,“我是珠江河里的淡水鱼,怎么能去海里?”
欧阳东则在回归前就回到了深圳蛇口,留在南山区文化馆跟一群中老年表演者一起排演《红色娘子军》,他演洪常青。他带领的金彩霞艺术团至今每周都会有两三次排练,他会组织,也会亲自参与排练。
刘梦熊写书布道,获得了“期货教父”的名号,他出任世界最大华资证券行京华山的首席顾问,1996年,完成了从商界到政界的转身,当时他是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的发言人,之后又很快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港人常用“跌落地也要抓把沙”来形容他。今年2月27日,因妨碍司法公正罪入狱的刘梦熊恢复自由。
为逐步恢复人气,他每周在商业电台做《梦熊有召》节目。在访谈中,他表示自己从不灰心丧气,在狱中看了很多之前无暇阅读的书籍,坚持每天看报纸,以免与社会脱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刘梦熊曾向记者描述自己从深圳游到香港上岸的经历,“当时我是穿着一条游泳裤到了边民的家里,我就说帮帮忙,我在荒山野岭与世隔绝了六天六夜,能不能把以前的报纸给我看看。他们一听愣了,说接待过成千成百的偷渡客,一进门都说饿死了有没有东西吃,冷死了有没有衣服穿,唯独我首先问有没有旧报纸。”
“我说当然,来到香港就是要竞争,知识就是力量。”刘梦熊的眼神突然认真起来。
如今,年过七旬的陈克治回忆在港的半生经历,他说《狮子山下》这首歌最切合自己——“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那时昼伏夜出,太阳下山后又充满信心去翻山越岭,歌里鼓励他们这些起跑线滞后的人积极看前,发奋图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翠、罗霞、钱笃诚、钱洛深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