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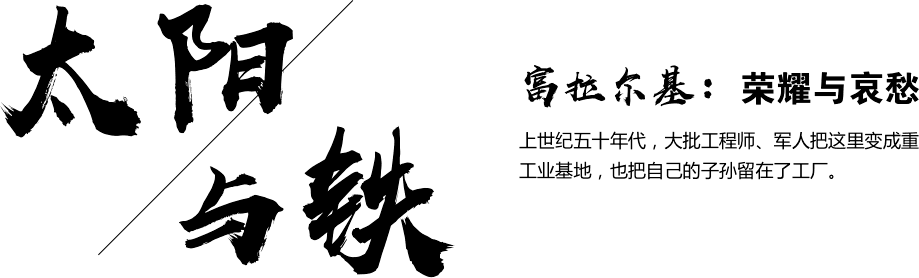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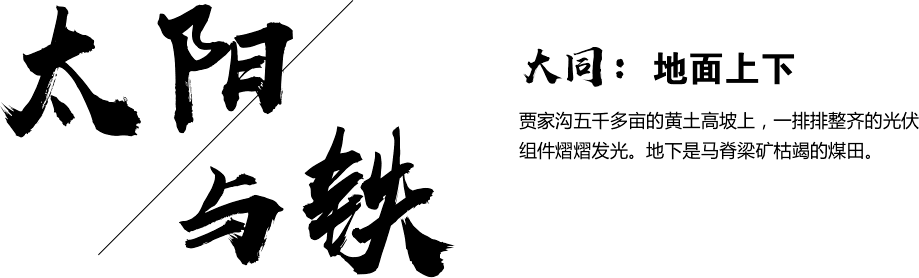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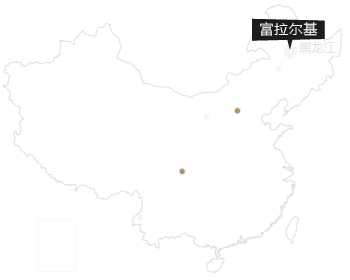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临近退休的职工,大多不希望后代进入工厂。他们说:“孩子小时候见到我们的苦。”
他们的父辈是拓荒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应国家的重工业战略,大批工程师、军人等,来到这里建设,让这个苦寒之地变成重工业基地,也把自己的子孙留在了工厂。
那时,因为有三个苏联援建的156重点项目,还有国家重点院校,富拉尔基逐渐成为科技和产业高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也汇聚到这里。大工厂有自己的中小学校、职工医院、公安局、闭路电视台、体育场。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人来做小生意,这里的人还不怎么看得上,自己可是老大哥,最早享受了工业化的阳光。
如今可不同了。这些工厂,炼钢的,化工的,纺织的,造玻璃的,大多已破产萧条。它们在破产之前,同岗位的工人工资,只有外面工厂的三分之一。
富拉尔基两代人的重工业城市记忆
中国一重情况并不赖。它是如今总部位置最靠北的央企。但重要的研发设计等部门,十余年前就陆续迁至沿海。
这些拓荒者的子孙们,本来不属于这里。只是还走不了,得照顾老人。
状况好一点的,每月靠着两三千元退休金,也能过得安逸。这里毕竟物价低,在健身房办卡,只要三百块一年。
而那些坏一点的,工厂破产,一次性买断工龄。二十年的工龄,折成八九万,甚至只有一两万。这就未免令人不平。
无论状况好坏,他们头上都还悬着一种风险——积下的职业病一旦发作,不知要花多少钱。
但日子还得过下去。“能吃得了苦,能遭得了罪,也能享受这个低水平的生活。”拓荒者的后代说。
要谋生计的人,在大家庭商场,租了摊位卖东西。领着退休金的人,组织集体舞表演,回味青春岁月。
年轻一代不太知道爷爷辈是怎么来的。有人在家啃老,或是做网络直播。
也有人想出去发展,但这并不容易。
18岁的吕静滢,是一重技师学院的学生。寒暑假期间,她去做服务员,两个月能赚三千多块。她想,往外走得有技能,就去学习美容美发。
而她的父亲还在工厂。“我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走出去。所以,我爸还不能退休。等我走出去以后,五年吧。他才能退休。最起码,我得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把他接走。”
红岸公园诉说着祖辈的辉煌,周恩来曾在这里远眺嫩江。嫩江沿岸有四座抽水泵站,早年每天将73260吨江水送到工厂,满足电力、冶金、机械、化工等生产用水。富拉尔基虽然临江,却时常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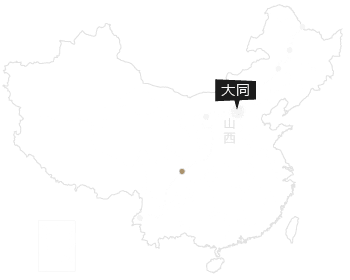
作为国家的能源基地,山西大同是缺水的地方。采煤耗水,煤电也耗水。
如今,在因被采空而沉陷的地面上,植物长不起来,却架起了大片太阳能组件。
大同市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是国家能源局“光伏领跑者计划”的首个基地。该计划于2015年发起,通过建设示范基地和示范工程,扶持光伏发电的先进技术和应用。
其中,同煤集团的左云县贾家沟光伏基地,装机十万千瓦。
贾家沟五千多亩的黄土高坡上,熠熠发光的光伏组件排列整齐。地下是马脊梁矿枯竭的煤田。要巡检所有方阵,开一天车都跑不完。
站长董国飞生于1984年,在大同市区长大,没见过以往矿区漫天煤灰的景象。在他的印象中,大同一直天空晴好,空气清新。这正是发展光伏新能源所需要的天气。

董国飞在贾家沟光伏基地。
“一定要小心。要是掉矿里去,你们到矿上找我。”董国飞开玩笑说。因地面沉陷,站上曾有工作人员不慎踩进坑里,一直陷到腰,最后被拉了出来。
两年前,董国飞为项目选址而来时,这里只有黄土和风。那时,附近村里只剩几户人家,沉陷导致房子裂缝。远远还能望见小煤窑工人住过的窑洞。
采煤沉陷区的土地,几乎没法用于其他产业。采煤破坏了地下水系,很难种植作物。因煤层被抽去,地基也打不牢,不宜发展工业。
“还是发展光伏,比较适合沉陷区,对自然的扰动很小。”董国飞时常见到野鸡野兔,从变电站旁跃过。山坡上架着各国的光伏组件,进行现场应用,比较转化效率等指标,找出最好的产品。这儿是个实验室。
董国飞每周接待各种光伏产品的供应商。贾家沟基地第二期项目,还要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各种供应商纷至沓来。他一周五天住在站上,每周末回家两天。要是站内做实验,或停电检修,以及出现其他状况,就不能回家休息。
董国飞的妻子是他研究生阶段的同学。2011年二人毕业,一起进入同煤集团。那时董国飞要去的是光伏制造部门,但因当时行业低迷,这个部门被取消。董国飞被分往他处。三年前,同煤拿到这个项目,他才重新进入光伏行业。
在整个同煤集团体系里,薪酬跟着职称走。董国飞夫妻都是中级工程师,每人每月工资大约三四千。比同行业低一些。
贾家沟这五千多亩土地上的十万千瓦装机量,大约只是同煤集团电力总装机容量的百分之一。而光伏基地还得看天吃饭。如果电站后台显示器上的抛物线塌陷了一块,很可能是天上飘来一片云或一阵雨。不像火电,可以稳定持续地供能。
光能目前不仅在数量上难以代替火电,还得与火电搭配上网,才能减弱对电网的冲击。在中国西部其他地方,因光伏发电不稳定,对电网冲击巨大,时常被弃而不用。但在大同,稳定的传统火电占了大头,使得光伏发电的波动不至于冲击电网。同时,这里临近中国北方的能源需求地,电能更易被消纳。因此,大同从未出现弃光状况。
煤仍然是动力的基底。
在大同矿区,矿工原先大多住在矿上的自建房,但那些房子因沉陷而不安全,人们被集中安置到了市区。晋华宫矿在云冈石窟边上,要是到这里上早班,矿工早晨最迟得五点半起床坐班车,下午五点半才能坐班车回到家。
除去开会和洗澡,矿工在井下一次至少工作六个小时。地下世界是三块石头夹一块肉,矿工在当中。土、风、气、水,都对应特殊的身体体验。
人的头上是土,为防止土压下来,就得用锚杆和锚索向上固定。
也必须防范风的事故,如果通风机出故障,井下瓦斯就会超限,随时可能因遇到火源而爆炸。
透水事故也很可怕。矿井之下,地下水从矿工的头顶流过,亿万年前沼泽的印记就像水的影子。而干到最后,矿工浑身内外湿透,就像壁上渗水的石头。

晋华宫矿老矿工马志斌在下井作业的入口处,他的工作面在地下300多米的地方。
晋华宫矿的工会干部,曾经领着职工家属,带上饺子,到井下的工作面去慰问。
“有个综采工作面,是低煤层的,人得爬过中间的支架,最多一米高。有个家属爬到中间,就哭起来,说自己不行了,出不去了。”
在这样的井下工作,人到五十岁,就很吃力了。
矿区一度繁荣,人丁兴旺。但总免不了风险与职业病。所谓煤矿安全规定是用血泪写成的,指的是每出一项事故,规定中就补入一些应采取的措施。
在晋华宫矿的生活区,曾负过工伤的老人,午后总在太阳下坐着拉家常。他们也许会想起那些更为不幸的人们。
建矿已六十年的晋华宫矿,如今职工有七千人,连家属有三万多人。眼下正在去产能。同煤集团要求生产减量,晋华宫矿年产量500万吨,今年限额是330万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井下不生产,给矿工放假。这也是之前没有过的。
同煤集团的高层领导,四月里轮流去各矿“讲形势,亮家底”。
“不能让一个职工下岗。职工就像老父亲,没有啥技术,也不能丢下,还得养起来。”同煤集团宣传部长赵立书特别强调,这是社会责任。
同煤集团还为有本科学历的集团子弟敞开大门。只要再去读个采矿专业,回来就能安排就业。虽然煤总有一天会采完,但大部分家长还想在自己眼前,把孩子的未来安排好——倘若不够优秀,还不如在大家庭享受温暖,哪怕是共度难关。
有不少矿上子弟,没有本科学历,仍想通过当兵复员的渠道,安排个井下工作。
“煤矿工人要求也低。盼企业煤价高点,多卖点钱,工资高点。回家能有个热乎饭吃,出井不用等车就能坐车回家,回家吃晚饭休息休息。”
“从小到大,都是晋华宫矿培育你长大的。没有这个煤矿,就什么也没有了。”
但上亿年积攒的能源,在一百年间,便已近枯竭。
胡焕庸线走廊一带的变动,早深埋于地下交错的构造中。侏罗纪时期的一片沼泽,经过地壳运动挤压,才变成如今的煤。